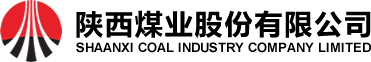天剛蒙蒙亮,窗臺上那盆野竹子就醒了。葉尖掛著的水珠晃了晃,被穿堂風一吹,吧嗒落在窗臺上,像誰輕輕敲了下桌子。這竹子是去年去四川朋友那里玩的時候帶回來的,在山里長了不知多少年,根須扎得深,移到盆里也沒改了性子,一個勁兒往上躥,倒也比辦公室里那些養在瓷盆里的文竹看著潑辣——像極了常年扎根在項目一線的職工們,皮實,有股子不服輸的勁兒。

我爺爺以前在村上當干部,家里堂屋的方桌上總擺著個粗瓷茶杯,泡的是商店里幾塊錢的便宜茶,梗多葉碎,喝著帶點澀。有回我放學回家,撞見鄰居王嬸往桌上放了袋雞蛋,紅著臉說多謝爺爺幫她孫子辦了入學,說完轉身就走。爺爺抓起雞蛋就開始追,倆人在曬谷場上拉拉扯扯,褲腳都沾了泥,最后爺爺從兜里摸出五塊錢,硬塞給王嬸:“雞蛋我收下,給我孫女補營養,但這錢你必須得拿著——我當這村干部,可不是為了占鄉親們的便宜……”
如今,我也工作了,在機關黨群部門做宣傳干事,桌上總堆著些印好的學習材料,字里行間都是“清正”二字。上個月籌備廉潔主題征文,有個生產一線的職工找過來,說剛給我QQ發了一篇稿子,想讓我幫忙“潤色潤色”,好讓他完成任務,完了請我吃碗泡饃。我打開他的稿子,里面簡單的寫著夜班時怎么盯著壓力儀器儀表,寫著檢修時手上磨出的繭子,雖然簡短,但卻帶著股鉆勁兒。“你這稿子不用潤色,”我指著剛印發的紅頭文件上“學思想、強黨性、重實踐”這句話給他看:“咱一線工人的故事,就像井場的鉆機,實打實才有力氣,你們生產一線那些師傅們愛崗敬業、艱苦奮斗、扎根一線的事兒,比啥修飾都有力量。”說著從抽屜里拿出本《榜樣》,“你看這里面寫的勞模,哪個不是靠真本事說話?”他愣了愣,撓了撓頭走了,后來那篇稿子登出來時,旁邊配著他滿手油污檢修機器的照片,字里行間全是一線井場鉆機的油味和師傅們揮灑汗水的咸味,比任何修飾都動人。
前陣子帶著部門的小王去一線拍宣傳照,給稿件積攢素材。項目乙方包工頭從工具房里拿出兩個玻璃杯,塞到我們手里,背身上印著“安全生產”四個金字。“拿著拿著,不值錢,泡個枸杞正好。”他笑的臉上的褶子都擠到一塊了。小王正要伸手接,我拉住他,對鮑總說:“您這杯子上面印著安全生產,就得留在工地上時刻提醒大家才對,我們辦公室里都有自己的杯子,這拿回去也用不上……”包工頭聽完尷尬的笑了笑,我指著不遠處正在運轉的鉆機,鉆頭正一寸寸往地下扎,“您看那鉆機,每往下鉆一米都得校準參數,半點馬虎不得。咱這人心里的秤,也得這么準才行呀。”他愣了愣,把杯子往工具房角落一放,說:“你這姑娘,說話跟鉆桿似的,直來直去……”
晚上回到家,兒子正拿著自己的小水壺給窗臺上的竹子澆水,扭過頭對我說:“媽媽,媽媽,你快看,我給它們澆水水,它們好像又長高了呀……”風從窗外鉆進來,帶著點土腥味。我望著正在澆水的兒子,又想起爺爺那只泡茶的粗瓷杯,杯子里泡的那些粗茶,浮起的片片碎葉,似乎懂了:原來清風從不是書本里的大道理,而是爺爺的那份堅持,是一線職工文章里的油星子,是把不該拿的杯子退回去時,心里的那份踏實。我扭過頭對兒子說:“果兒,你看,我們要像這竹子一樣,扎根要深,腰桿要直;還要像你澆花的水,不偏不倚,清澈見底——每一滴都落在該去的地方,不帶半分私心,也容不得半點混濁,滋養的草木生長,也映得見天地清白。只有這樣,我們的日子才能過得踏實,連夢里都是松快的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