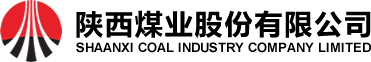在5月8日陜煤集團召開的抗擊疫情復工復產先進集體先進個人暨文明單位勞動模范陜煤工匠表彰大會上,陜西煤業扶貧第一書記晏彬榮獲陜煤集團2018-2019年度勞動模范榮譽稱號。晏彬在扶貧工作中沖鋒在前,為扶貧村脫貧致富作出了積極貢獻,讓我們從他深情的自述中,一起聆聽建功扶貧攻堅戰場的感人故事。
讓幸福之花開滿江河
從2017年4月我來到秦嶺深處的陜西漢陰縣雙乳鎮江河村擔任第一書記,至今已是第三個年頭。
走家串戶識江河
我是陜南人,對陜南的生活環境相對熟悉,這里的青山綠水也讓我找到了家鄉的感覺,更堅定了我要一展拳腳,帶領這里百姓富起來的決心。
江河村山多川少,林多地少,土壤貧瘠,農作物產量低,工礦業稀缺,勞動力流失嚴重。村中老弱婦孺多,貧困殘疾比例高。上任之初,我就去走訪農戶,與老黨員老干部、普通村民交談閑聊,實地調查了解村里基本情況。
江河村多湖湘移民后裔,方言湖南湖北味濃重。在入戶走訪中,剛開始村民說的很多話并不能完全聽懂。一遍不懂我就再問一遍,連猜帶想地去理解他們要表達的意思。時間長了,我的陜南口音也有了江河味。多次入戶后,有的老人去一次兩次還是不認識我,我就繼續去,每次去都要問:“你認得到我不?”就這樣一來二去,他們的回答變成了:“認得到,你是晏書記嘛。”后來我又想了個辦法,把我的名字和電話號碼加粗放大,打印出來,挨家挨戶貼在貧困戶的墻上,讓他們記住我,有事就找我。
從村部到江河村后山的農戶家有近二十多里山路,單靠步行入戶是不大可行的。車到不了最遠的村民家,只能向村支書借來摩托車去。
一次在村里最遠的一戶村民家中了解情況,看到屋里堆滿了剛從地里刨回的土豆,就問他們銷路咋樣,賣價又如何?得知這些土豆并不好賣,回去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怎么能為他們找銷路。
當時天下著小雨,而安康山民的房屋多建在半山上,坡陡路窄,僅能容一人行走,一下雨就成了排水的水路。一不留神腳底一滑,身體失去平衡,摔了下去,手臂被路邊的亂石擦破。回去簡單處理后,土豆的事又上了我心頭。詢問村干部后,得知村里還有15000斤左右土豆待售,就利用朋友圈呼吁親朋好友幫忙宣傳。很快便有人發來信息詢問,富硒土豆終于走出了大山。

(晏彬(右)在荷田中查看生產條件)
一波三折搞產業
在我到任之前,村里已引進千畝核桃園、拐棗種植和百畝絞股藍種植,部分貧困戶已經從中受益,但仍有很多居住偏遠和身體狀況差的貧困戶沒有加入。單靠傳統小農經濟或外來企業投資,農民增收不足,脫貧效果不明顯。我思考還是得靠發展集體產業來帶動經濟。
當我在一次支部會議上提出要發展村集體經濟時,不少干部面露難色,一位委員說到,“搞農業,投資大、風險高、收益少,搞啥賠啥。”
搞產業一定要靠技術、嚴管理,我知道一些地方產業搞得好,就帶領村干部到縣內的觀音河村、藥王村以及漢濱區、四川萬源,學習水產、黑豬養殖、黃花種植等產業。看到別人的產業搞得紅紅火火,村干部們看著心動,想著激動,態度也跟著發生轉變。
我們又找到鎮里主管農業的副鎮長,看看有沒有回鄉創業的能人大戶愿意和我們一塊搞產業。恰巧水產養殖戶方榮軍想搞小龍蝦產業,苦于找不到合適的池塘。我就領著他去了村里的安良水庫。
見到水庫下游30畝廢棄的池塘,他說,“真是個好池塘呀,上頭是個大水庫,水源有保障。要是我們在這搞小龍蝦養殖,肯定沒麻達(沒問題),還可以挖掘附加值嘞。”
看他面露喜色,我跟他說,“只要你技術沒問題,你出一部分錢,我們出一部分錢,把土地流轉過來,一起弄。”就這樣商議后,村集體與養殖技術人才共同出資,建設了特色養殖基地30畝,養殖小龍蝦、土雞等。
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基地效益良好,可受制于村里地形,無法擴大規模。這時老方看上了鄰村的100畝池塘,覺得非常適宜擴建,但本村的村干部卻不愿意了,“我們村的錢,怎么能投到別的村去?”對此我提出,要發揮我們已經形成的養殖優勢,就得擴建,租別人的地也是為了我們村集體受益。
好不容易本村達成一致,到了鄰村又碰了釘子。鄰村的干部說,“我們的池塘不能租,只能合作。怎么養得聽我們的。”本來我們的村干部就有疑慮,這下直接一拍兩散了。兜兜轉轉了一圈,原來是鄰村已形成千畝荷塘景觀區,害怕我們搞養殖破壞了他們的整體規劃。
和老方商量后,我們決定嘗試蝦藕混養。再次對接時,雙方將不破壞總體規劃及三年承包經營事項全都清楚地寫到合同里,終于消除了所有疑慮,蝦藕混養項目總算落了地。
有了短期見效的特色養殖產業,我的心里還是不夠踏實。要保證長期不返貧,必須有長期產業來支撐。問題是長期產業投資大,見效慢,選擇起來更需慎重。雙乳鎮已有嘉田農業建成的300畝富硒黃桃產業基地,技術、銷路有保障。經過勘測,本村的土質也適合黃桃種植。于是我們找到嘉田農業協商達成了共同出資建設百畝富硒黃桃種植示范基地的協議。
基地建設推進并非一帆風順,征地初期就遇到三組的幾戶村民不同意流轉土地。我們只好挨家挨戶做工作,村民鄧良貴說,“我們種地一年還能換好些錢,這點流轉費兩桶油都買不到。”我說,“土地流轉給合作社,既能拿流轉費,在里面務工每天有100塊工資,干一個月就頂你一年了,自己種地還得看天吃飯。”通過苦口婆心的思想開導,終于說服了村民,將土地流轉給合作社,完成了百畝富硒黃桃基地。
有了種養殖基地后,村民可以通過務工、土地流轉、合作社分紅增收。增收的大頭在務工,對弱勞力的帶動卻不明顯。我又思考,有沒有讓弱勞力也能參與其中的產業?
一次和朋友聊天,他告訴我奠儀用品技術簡單、勞動強度低、市場穩定,“你們想搞,我介紹你們去漢中看看。”
說干就干,利用村里安良小學閑置的校舍,經過簡單裝修,我們的紙藝廠就辦了起來。與漢中的大廠簽訂了保底收購協議,又請來技術人員,一期培訓了10名工人。經過三個月的練習,熟練工每月的收入可達2000元以上。
工廠有了效益,村干部干事創業的激情也被激發了出來。村干部史方軍主動申請去工廠專職負責運營,“從不敢搞產業到爭著搞產業,我的思想在不斷改變。我們工廠已經籌劃進入第二階段,面向全村弱勞力計件制作生產竹架,帶動全體村民勞動致富。”
目前,江河村已形成“一廠兩基地”的集體經濟發展格局,種養殖業長短結合,一產二產多元發展,產業扶貧的實踐正火熱推進。

(晏彬在楊凌第26屆農高會上推介產品)
媳婦生娃我住院
晨聞雞叫,夜聽蟬鳴,駐村的日子因忙碌而充實。與村民和村鎮干部的朝夕相處倒也融洽,但疏于對家人的照料讓我愧疚。
年邁的父母遠在漢中老家,幾個月才回去探望一次。妻子在西安,只有假期才能相聚。我只有盡量把注意力轉向工作來分散聚少離多的愁思,白天入戶晚上處理材料。有時一早去山里的村民家走訪,到下午才能回來,有時大半夜還在加班。長期飽一頓餓一頓,飲食與睡眠同時的不規律,讓身體素質明顯下降,頭發也掉得厲害。
2018年6月29日晚飯后,突然覺得肚子疼,想著撐一下,或者喝點熱水就沒事了。誰知越來越不對勁,微痛逐漸轉為劇痛,疼痛難忍。村干部知道后立即驅車將我送到安康市中心醫院,檢查為急性闌尾炎,當即做了手術。
第二天,躺在病床上的我身體雖有好轉,但想著手頭還有一大堆事等著我,加上妻子臨產,心里很是焦急。為保證村上產業繼續推進,就聯系單位,讓同事朱兆偉過來銜接工作。他當天晚上趕到醫院,與我對接了小龍蝦養殖選址等事項便奔赴江河村。
7月3日凌晨兩點多,妻子打來電話說快要生了。聽到這個消息,還在病床上的我萬分焦急,有種束手無策的感覺,此刻不出現在她身邊讓我深感失責。無奈之下給單位同事魯建民打了電話,拜托他去我家把妻子送往醫院候產。
當天下午,女兒平安出生,我終于松了口氣。后來魯哥打趣道,當時護士抱著嬰兒走出產房,以為他是孩子的父親,還讓他猜孩子是男是女。
這次生病住院,村鎮干部和單位同事的幫助讓我非常感動,而這個扶貧寶寶的誕生,則是我駐村工作中得到的最好禮物。